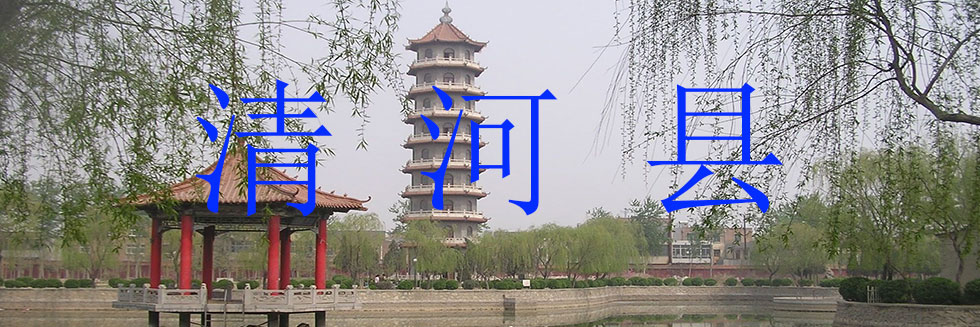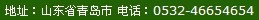|
黄河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聚集区,这从许多黄河口人至今未改的方音里就能感觉出来。鲁西人、潍坊人、胶东人、东北人,天南地北的农垦人、五湖四海的油田人……不同时期,不同性质的移民,为黄河三角洲带来了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民俗、不同的气质、不同的禀赋,也让古老而年轻的黄河三角洲拥有了海纳百川、兼收并蓄的广阔胸襟。 “问我祖先来何处?山西洪洞大槐树。”“祖先故居叫什么?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“要问老家在哪里?直隶省的枣强县。”和山东乃至全国许多地方一样,黄河口的人民也都熟悉这样的移民歌谣。多少代人的口耳相传,这些苍凉朴实的民谣依旧回荡在广袤的黄河口上。从中既能读出黄河口早期移民对故乡的无限眷恋,也能读出今天的黄河口人追本求源的深情呼唤。 遥想当年,黄河口人的祖先,推车担担,扶老携幼,沿了大清河两岸,循着五尺官道,从祖一辈父一辈聚族而居的三晋大地,一步三回头地来到这片寂沉的古战场上,耕种养殖、休养生息。多少年沧海桑田,他们在大河尾闾、渤海湾畔重新建起了自己的温馨家园。同样是聚族而居,同样男耕女织;同样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他们最终将这里认同为家乡,却将祖籍文化里那些美好的东西继续发扬光大,同时也将一份厚重的移民情结深深烙印在了黄河口文化里。 元朝末年,因为连年战争,疫病流行,大清河下游已经是人烟稀少。一方盛产五谷、绕有鱼盐的热土,因为战乱,复归荒芜。溯河而上,因为同样的原因,整个中原地区也是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。刚刚走上整治舞台的朱明王朝,为了巩固政权,充实国库,稳定民心,不得不考虑全国农业经济的统筹发展。洪武三年,明朝中央政府制定了移民屯田的复兴政策,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垦殖的非常之举。而早在一年前,从洪武二年至永乐十五年的50年间,仅正史有记载的大规模移民就有18次之多,辐射今天共和国版图上的18个省(市)余县(市、区),如今黄河三角洲上个县区均属于移民安置范围。随后,还有相当数量的移民从直隶枣强陆续迁来。 年编纂的《利津县薄氏族谱》记载,薄氏“始(迁)祖讳庸,自有明洪武二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城东南15里薄村迁来利津县樊家寨境,遂以姓名庄(薄家庄)。”广饶县苏王村《苏氏家谱》记载:“始祖苏文强于明洪武二年自直隶枣强县迁此立村”。广饶县北徐楼村《徐氏家谱》记载:“洪武二年缪中元及其三子缪守自枣强迁此立村”。黄河口地区其他姓氏的族谱当中,也都有着类似的记载。 所谓“移民就宽乡”。明初政府移民的目的,一是为了让普天之下再无赤地,二是为了让农民人均占有更多耕地。与百万人口离乡背井的暂时凄凉相比,这里边深远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只是不知道,当晋文公臣民的后裔长途跋涉,初次登上渤海湾畔这片土地,首次邂逅齐桓公臣民的后人时,他们打的第一声招呼是什么? 没有更多的声像甚至文字记载来记录那段移民搬迁演进的历史,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大概只有家园、房屋和农具的变迁。从因陋就简的土坯茅屋,到今天的砖堂瓦舍,这是一种变迁,从当年的木轮小车,到今天的联合收割机,这也是一种变迁。黄河口人最终在这片年轻的土地上,建成了自己的美丽家园。 清咸丰五年(年),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(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内)决口,主流东行,夺大清河道入海。一夜之间,大家门前的一脉清河变成了滚滚黄河。随之而来的,是那种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的难以抗拒的变迁。值得庆幸的是,黄河携带来的大量泥沙,在入海口一带迅速沉淀、淤积,最终形成了大片的新生陆地。对于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当地居民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大大的福音。 位于黄河入海口两岸的大片新淤土地,当时分属山东省的利津、广饶、沾化、无棣等县。因为其大部分在利津县境内,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之为“利津东北洼”。由于成陆较晚,加之土壤的自然改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,直到清朝末年,这片广袤的新淤地依旧是人烟稀少、荆棘丛生、一派荒凉。直到20世纪初期,许多本地人、外乡人才开始尝试着来这片新淤地上拓荒耕种。那时节,“利津东北洼”仍然是这片土地唯一被认可的名字。 民国初年,鲁西地区遭受特大水灾,灾民衣食无着,被迫四处流浪。为了安置难民,但是的山东省政府曾专门设立“滨蒲利广沾棣淤荒设治筹备处”,将灾区难民迁到黄河口开垦荒地,自谋生路。年,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,派其治下的第五十九旅来黄河口屯垦,一方面圈占新淤土地,一方面强行占领散户移民开垦的土地,按照官职大小分赠官佐部众。由此,在屯垦集中地带出现了王营屋子、刘家屋子等若干村落。这成为民国年间针对黄河口的第一次比较集中的移民行动。 年,黄河在山东省鄄城县决口,滔滔河水过处,菏泽、郓城、嘉祥、巨野、济宁、金乡、鱼台等县尽成泽国。数以万计的灾民携妻带子,流离失所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鲁西灾民余人来黄河口垦殖,每人编为一个大组,划拨新淤地让他们开垦耕种。于是黄河口新淤地上逐渐形成了“八大组”及一村、二村、三村……二十五村等众多移民新村。这是民国年间针对黄河口的第二次集中移民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不断发展,“八大组”逐渐成为这些移民新村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年4月,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决定以“八大组”为中心建立永安镇。不久,省政府又决定在此设立新安县,并在八大组设立了“新安县筹备处”、“垦区筹备处”。从此,“垦区”成为黄河尾闾这片新淤土地的名号。 然而,国民党政府在垦区设县的计划还未付诸实施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地方当局弃地而走,垦区由此沦为日寇和土匪争相掠夺的对象。年7月,这里建立起了垦区抗日根据地,两年后垦利县在此诞生。“垦利”就是“开垦利津东北洼”的意思。此后的短短几年间,近10万名外地移民陆续来此定居垦荒。 年,鲁西南遭受特大水灾,东平、巨野、寿张、梁山、嘉祥等县受灾群众,来到黄河口。年,为修建东平湖水库,东平、梁山、长清、平阴、青岛、济南等地移民1.7万多人来到黄河口的利津、垦利两县落户。年,黄河口地区再次安置梁山等县库区移民5余人……黄河口成为五湖四海人共同的家。 位于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垦利县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县。据统计,目前该县境内已经聚集了全国13个省个县的移民。同一个乡镇、甚至同一村庄,都会有不同的习俗、不同的乡音。这里是中国民俗文化的标本,这里是团结和睦大家庭的典范。尽管乡音未改,尽管自成村落,但随着彼此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个领域团结协作步伐的加快,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生产生活、风俗习惯上,都有了更多的认同。 20世纪50年代,国家先后在黄河三角洲上设立了渤海、黄河、广北三个国营农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养马场。这些机构尽管在名称、所属和职能上几经变更,但他们基本是以农垦、军垦的形式出现在黄河尾闾、渤海之滨的。而随着这些农垦、军垦机构的建设发展,一大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农场人、马场人最终在这里落户生根,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战斗,成为了黄河口名副其实的拓荒者。 解放军官兵、公安干警、城市知青……大规模的农垦和军垦为黄河口带来了整建制的新居民,也为这方开放的土地带来了更多类型的文化元素、生产方式和民俗习惯。规模化的农场作业、先进的农业技术、探索性的经营方式,使得他们在生产、生活、文化、教育等等各个方面与地方群众形成了优势互补。不管农场还是马场,他们在黄河口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,他们始终与当地居民水乳交融,共兴共荣,他们在影响这黄河口人,黄河口人也在影响着他们。最终,他们都把自己视为标准的黄河口人。 20世纪80年代中期,随着东营市的诞生,这片荒原上战天斗地30年的数十万胜利油田人彻底结束了居无定所的“游牧生活”,住进了城区的高楼大厦。他们成了东营市的市民,他们完成了一个移民部落与另一个整体部落的真正融合。也许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,随着企业改制工作的不断深化,油地协作的日子还会很长很长。但作为黄河口人,作为东营市民,他们的心灵早已息息相通的。 黄河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,黄河口是一个多种自然景象、文化现象、民俗事象交相辉映的地方。黄河口所拥有的黄河文化、海洋文化、移民文化、古齐文化、三晋文化、燕赵文化、石油文化、农垦文化、商业文化、水运文化在相互启发、相互影响。黄河口的古老居民与山西移民、河北移民、鲁西移民,甚至福建移民、三峡移民在生产习惯、生活习惯、节日习俗、婚庆习俗等方面在互相碰撞、互相借鉴。 有民俗研究者称,经济发展从本质上决定了黄河口的生活习惯。来自天南地北的黄河人在节日、婚丧、民居、生产等习俗方面都存在删繁就简的倾向。黄河口人注重实际,有山西人勤劳俭朴、善于持家的特点;黄河口人注重形式,与古齐国人注重仪表、财富外露、衣锦居陋的特点相吻合。而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现代都市的形成,石油文化、现代都市文化等对黄河口移民文化的大融合产生了巨大影响。 文字、图片来自网络,由东营众筹整理编辑,如有侵权,请联系小编,我们将及时删除。 赞赏 长按鍖椾含鐧界櫆椋庢潈濞佸尰闄?鍖椾含娌荤枟鐧界櫆椋庡幓鍝
|
当前位置: 清河县 >独一无二的东营,不管是地方的,还是油田的
时间:2017/7/21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吴传全清河坝的婆娘
- 下一篇文章: 雄安未来这么好,和你有什么关系看完你就
- 热点内容
-
- 没有热点文章
- 推荐文章
-
- 没有推荐文章